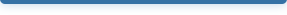◇徐持(法學研究所)
東京審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社會對日本戰爭罪行進行清算的重要司法實踐,也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確侵略戰爭為國際罪行并追究個人刑事責任的國際審判。盡管其歷史意義深遠,但東京審判長期以來被不同程度地簡化、誤讀甚至政治化。許多西方著述在談到為何寫作或討論東京審判時,普遍認為東京審判受到了有意無意的遺忘。這種“遺忘”,既是指與紐倫堡審判的大量著述形成的鮮明反差,更是指東京審判的正面意義受到了質疑。重新審視東京審判,不僅關乎歷史正義的還原,更關乎對國際法治演進的理解與未來和平秩序的構建。
圍繞東京審判的爭議和誤讀,主要源于三方面因素。一是由于日本學界“標簽化”的“東京審判史觀”,東京審判的司法特性一度被遮蔽。進入21世紀以來,日本右翼更是不遺余力地否定東京審判,狡辯其為“勝者的正義”。即便在知識界,研究者也多將研究焦點置于審判周邊的政治外交問題。這樣的視角難免將司法事件與國際政治、國際外交混為一談,較少涉及法庭審理的法源法理、罪名設置、犯罪認定、審理程序、庭審證據、判決意見等研究內容,回避了審判的“法的價值”這一核心問題。二是審判持續時間長達31個月,程序復雜、語言多樣、證據龐雜,“漫長的審判”導致公眾注意力逐漸渙散,輿論熱度消退,甚至引發“效率低下”“程序不公”等批評。三是東京法庭部分法官發表的反對意見和個人意見造成了令人始料未及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印度法官帕爾提出的“全員無罪”個人意見書,被日本右翼片面利用,扭曲為否定日本戰爭罪責的依據。這些因素交織,使東京審判的法治內涵和歷史貢獻長期被遮蔽。
然而,回歸法律與程序的本質,便可發現東京審判具有不可替代的司法價值和開創意義。首先,在法庭機制方面,東京審判雖名義上由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主導,但實際運作仍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為準則,體現了多國參與和司法公信的特點。法官來自11個不同國家,不論在形式上還是實質上都是一場名副其實的國際刑事審判。檢方按照憲章和程序規則行使了起訴裁量權,辯方享有充分的訴訟權利,實現了控審分離,體現出高度的法律審慎和程序公正。
其次,東京審判在被告人權利保障和程序正義方面亦有重要建樹。當時在日本國民中還存在著“像戰爭罪犯這種可恥的人不需要辯護”的情緒,但東京法庭除為被告人聘請日本辯護團外,還配備了美國律師,辯護時間達187天,遠超同期國際審判的標準。這讓很多日本國民和法學家深受震撼和感動,以團藤重光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法學家對東京審判給予充分的正面評價,認為可以將之視為“能對世界和平間接做出很大的貢獻”,是“劃時代嘗試的國際審判”。盡管存在翻譯延遲、程序冗長等問題,審判仍致力于在戰后初期國際法尚不完善的背景下,建立一套盡可能公正的司法程序。這些實踐為后來《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的制定提供了寶貴經驗。
最為重要的是,東京審判首次在國際層面系統闡釋并認定“反和平罪”,將策劃、發動和執行侵略戰爭定義為犯罪行為。法庭未陷入“侵略定義”之爭,而是通過具體案例——如日本在中國東北、東南亞及太平洋地區的軍事行動——實證其侵略性與違法性。這一法律認定,不僅填補了傳統戰爭法體系的空白,更奠定了現代國際刑法中“侵略罪”的法理基礎。2017年,國際刑事法院通過侵略罪定義,某種意義上正是對東京審判法律遺產的繼承。
東京審判也是一面鏡子,反映出國際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的困境與挑戰。審判期間面臨的證據獲取困難、語言障礙、文化差異、國家間政治博弈等問題,至今仍以不同形式困擾著國際刑事法院和其他國際司法機構。而從審判后的歷史進程來看,冷戰格局的形成、美國對日政策的轉變、日本戰爭責任問題的懸置,均顯示出國際司法無法完全脫離政治語境獨立存在。這一現實警示我們,國際法治的推進既需法律技術的完善,也需國際共識與國家意愿的支撐。
中國與東京審判的關系尤為特殊。作為日本侵略戰爭的最大受害國,中國不僅是審判的參與國,更是歷史正義的訴求方。然而,由于當時國內政局動蕩,中國在審判中的角色長期被國際學界忽視。直至近年,隨著東京審判相關檔案的整理出版,中國學者開始系統重構中國與東京審判的歷史關聯,并從法學、歷史學、國際關系等多學科角度推進研究,《重新發現東京審判:尋求和平與正義的國際法治》正是為這一轉變所做的努力,不僅有助于還原歷史全貌,也在提升中國在國際法治體系中的話語權方面進行了有益探索。
當前,全球秩序面臨不確定性,地區沖突和國際爭端頻發,國際司法機制的作用與局限愈發凸顯。在此背景下,重拾東京審判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東京審判告訴我們,國際司法不僅是懲治戰爭罪行的工具,更是規范國家行為、維護人類共同價值的努力。盡管過程難免摻雜政治因素,程序未必完美,但它代表人類試圖以理性而非復仇回應暴行的勇氣和理想。
對中國而言,深入參與國際法治建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立足自身歷史與實踐,貢獻東方智慧和中國方案。東京審判研究不僅屬于歷史,也屬于未來。它要求我們以更加開放的對話、更加堅實的學術努力,繼續探尋正義與和平的道路。而這正是“重新發現”東京審判的真正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