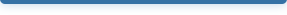◇楊霞(民族文學研究所)
金真慧(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
2025年10月13日,全球婦女峰會在北京舉行,習近平主席在開幕式主旨講話中指出:“中國堅持將婦女事業融入中國式現代化宏闊實踐。經過多年努力,中國婦女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1995年9月,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這場跨區域、跨國別、跨種族的婦女工作者、各行業女性代表的盛會,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女性會議,并擲地有聲地提出了“婦女權利即人權”的核心主張。大會通過的《北京宣言》《行動綱領》成為指導全球婦女事業的綱領性文件。金秋十月,北京世婦會愿景依舊在全球婦女峰會賡續,女性話題越來越被全社會、全世界關注,每一次女性群體的發聲、每一屆婦女會議的召開都在積極倡導女性權益,都在推動社會對女性群體的正視與認可,促進女性的全面發展。新時代中國多民族女性無論是在科學研究、社會分工、生存境遇、文學創作、大眾傳媒還是社會輿論領域,都在不斷發聲,傾覆對女性的偏見與固有印象,重喚被遮蔽和忽略的女性光輝。
從“被書寫”到“自主書寫”的轉變
新中國成立以來,多民族女性文學經歷了萌芽、覺醒、成熟三個階段,實現了從“被書寫”到“自主書寫”的轉變。新中國改變了女性的傳統地位,同時賦予她們從未有過的歷史機遇。生活在天南地北的女性作家開始意識到,這廣闊世間的角落存在著與自己有相似經歷的另一個“自己”,她們雖存在地域、民族、階層、性格、職業、學歷的差異,但在一體共生之中,民族的、女性的、藝術的表達掙脫枷鎖,破土而生,綻放出多民族女性文學的多樣之花。
彝族當代第一位女作家李納的短篇小說《姑母》《女婿》《婚禮》,自然質樸,簡明流暢,小說中的女主人公無論遇到何種境遇,都不會自暴自棄、自我沉淪,而是在樂觀中重塑自己的人格與精神,這種獨立人格是李納寄托于婦女身上的女性意識,是毅然決然投身革命的女性形象。藏族女作家益西卓瑪出版了藏族文學史上第一部女性作家創作的長篇小說《清晨》,為當代藏族文學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她沉靜敏銳、滿懷深情地書寫了她深愛的祖國和家鄉發生的巨大變化。佤族文學史上第一位女作家董秀英的處女作《木鼓聲聲》,被譽為“佤族文藝寫作敲響的第一聲木鼓”,終結了佤族沒有書面文學的歷史。朝鮮族女作家許連順的作品則聚焦女性生存境遇,通過描寫女性在婚姻、家庭、工作中的處境展現改革開放時代背景下朝鮮族女性群體的心靈變遷,以及她們在這一歷史階段的自我反思與迷茫。1991年回族女作家霍達憑借《穆斯林的葬禮》獲“第三屆茅盾文學獎”,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少數民族女作家,她細膩清麗的文筆展現了民族文化在傳承與創新中的能量。霍達的獲獎觸發了多民族女性文學的創作自覺。
追問女性自我生命意識存在的意義
當人類文明發展進入快車道,逐步邁進信息生產、知識生產與智能生產的全新時代,這一階段的多民族女性文學受家國意識、民族精神及個人經歷的影響,開始追問女性自我生命存在的意義,思索自我與廣闊社會間的關聯方式,由此彰顯出多民族女性文學內省的能量,女性敘事力量不斷增強。中國多民族女性文學創作者井噴式涌現,參與到創作、譯介、出版等文學生產活動中,女性文學作品不斷在文化市場亮相,她們在“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以及“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等國家級獎項評選中的獲獎頻率,以及作品所涉獵的題材范疇,表明中國多民族女性文學正在喚醒自我的內在意識,通往女性心靈的精神本原,以獨特、細膩且深厚的女性敘事力量獲得公眾的認同。女性作家站到各種領獎臺,代表了女性書寫更主動、更廣闊的可能。
滿族女作家葉廣芩的中篇小說《夢也何曾到謝橋》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鮮明的京味語言特色,平靜克制、哀而不傷的家族敘事,既有對糟粕文化的批判,也顯現出對傳統文化沒落的嘆惋。滿族女詩人娜夜憑借《娜夜詩選》獲得“第三屆魯迅文學獎”,娜夜的詩句蒼茫、憂郁、節制,她以豐富的想象力抒發愛、憂郁與贊美,具有女性詩人鮮明的細致和敏感。回族女作家馬金蓮憑借短篇小說《1987年的漿水和酸菜》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馬金蓮善用散文的筆調運轉流淌的生活細流,堅持用質樸的文字表達真摯的情感,捕捉西北鄉村廣大底層普通人群的生存和生活圖景。女性文學始終彰顯著對人性至善的堅守,為消解性別偏見與文化偏見、努力尋求真正理解女性精神世界開辟了道路。
個人話語、民族話語和
國家話語的交融性敘事
新時代最突出的文化特征是多元融合與價值重塑,既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又在全球化與數字化浪潮中構建具有當代中國特色的文化認同,形成“新的文化生命體”。“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截至2025年已評選十三屆,新時代“駿馬獎”作品明顯表現出承續使命與創作轉型,寫作由單向度線性敘事轉向多向度的空間性交融敘事,女性文學創作從自我的個人記憶轉向對土地和時代更為遼闊的生活與歷史的一次范式轉型。多民族女性文學以其獨特的創作優勢,塑造了涵蓋不同語言、民族、職業、文化背景與生命經歷的女性形象。
在社會轉型、少數民族文化保護政策的多重語境下,她們以淳樸、豐美、深摯的自我重述偉大的時代。藏族女作家梅卓《神授·魔嶺記》,佤族女作家伊蒙紅木《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報告》,土家族女作家徐曉華《那條叫清江的河》,壯族女作家黃芳《落下來》,蒙古族女作家娜仁高娃《馱著魂靈的馬》……這些作品像一串串優雅、圓潤的珍珠,串聯起多民族女作家筆下多彩、凝重的生活。維吾爾族女作家阿舍的長篇小說《阿娜河畔》,通過邊疆移民、軍墾戰士與當地少數民族在阿娜河畔共同開墾土地、建設家園的歷程,描摹了個體命運在時代洪流中的沉浮,再現了邊疆開發“荒漠變綠洲”的壯闊圖景。藏族女作家尼瑪潘多《在高原》講述的“西藏故事”,兼具“本土立場”與“他者視角”,既承載著特定的民族文化基因,又折射出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會階層女性的真實生存狀態,女性形象的豐富性、復雜性和深刻性被更深入地書寫。女性書寫不再局限于個人話語,而是個人的交往交流與時代變遷相裹挾的家史、民族史、國史并行的融合性敘事,在可見的豐盈與可感的遼闊中呈現出女性視角的新話語、新坐標、新世界,為中國文學整體格局提供了豐富的象征性樣本。
“行之茍有恒,久久自芬芳”,全球婦女的發展史、中國多民族女性文學的發展史時刻在印證,一場場世界性的女性對話開拓了女性話語空間、豐富了女性書寫語境,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話語被關注,被納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體系中,清晰地折射出全球性別平等浪潮對文化和文學領域的深刻影響,女性故事得以被廣泛看見,女性文學與新時代同頻共振,正在經歷一場更深刻而全面的轉型時代。女性文學不再是“特例”,女性自我書寫、女性共同體意識的內涵、流變以及與不同空間各民族文化構成或隱或現的親緣關系,形成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多元共生、互動循環的有機生態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