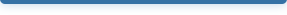今年以來,全球召開多場以“全球南方”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學者討論的主題聚焦全球治理、政治制度、經濟發展和社會治理等,但這些討論同時又凝練為一個問題:“全球南方”如何在知識層面解釋“全球南方”?
全球南方國家的崛起或許是近些年國際格局中最為突出的大事。這些國家的崛起不僅體現在國際政治與經濟領域,還體現于自身知識生產主體性的發現和確立。全球南方應由全球南方國家來解釋的呼聲,反映出全球南方國家學術界關于知識生產主體性的覺醒。
本報記者采訪了來自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的多位學者。受訪專家梳理了當下最受關注的全球南方國家知識生產議程:一是發現并放大共通的核心議題與理論關懷;二是拆解歐洲中心主義的隱性認知框架,批判并超越西方現代化話語霸權;三是為支撐可持續發展并構建與之相匹配的身份認同開辟新的理論空間。它們預示著南南學術共同體已在全球范圍悄然成形——它以自主知識生產為共同實踐,進而將關于全球南方國家知識生產的觀點碎片整合起來,展現出一個呼之欲出、以去“西方中心主義”為核心訴求的知識生產新圖景。
打破“知識的終極闡釋者”幻覺
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當前,全球南方國家知識生產的最大障礙是對西方權威的盲從迷信,甚至形成一種“知識的終極闡釋者”幻覺。它就像一塊“烏云”,遮蔽著全球南方國家的知識生產。
“全球南方國家必須打破‘西方是知識的終極闡釋者,我們只是原始數據供應地’的二元對立思維。”塞內加爾達喀爾謝赫·安達·迪奧普大學文學與人文科學院歷史教授馬馬杜·法勒(Mamadou Fall)說。在他看來,“原始數據”本身不自帶意義,如果缺少一套特定的理論框架、概念工具與話語體系,外部讀者尤其是西方讀者便無法從全球南方國家的視角解讀。因此,當務之急是讓全球南方國家發出世界聽得懂的獨立聲音。“而真正的挑戰在于理解,為什么某種特定話語秩序能夠如此頑固地一再強加其片面性,全球南方國家又該如何擺脫這一困境。”法勒說。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社會研究所研究員兼教授費和平(Fernando Vizcaíno Guerra)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剖析了西方認知論的政治化路徑。自20世紀90年代起,美國與歐洲借“人權”話語外衣,強勢輸出自由主義,將極端個人主義和西方式民主奉為唯一不容置疑的未來。該模式在全球南方國家間廣泛擴散,拉丁美洲尤甚。所謂的“知識外交”伴隨資本流動、貿易協定、安全項目、國際認可,以及精英大學、多邊機構與學術排名,共同構成認識論的“世界警察”,只承認與西方式民主合拍的思想形態。如今,這套機制借助數字跨媒體及其服務于全球權力的算法,對文化與科學范式施加深層次的控制。
法勒分析稱,西方認識論雖然主導著世界,卻是基于一種幻覺:它把世界想象為單一中心,并不斷加固這一認知框架。這種“幻覺”遮蔽了英國科學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在《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中反復使用的“河流匯入大海”比喻:來自亞洲、非洲和歐洲的不同文明猶如不同河流匯入同一海洋一般相互交融,在中亞和撒哈拉地區實現了融合。不同文明(如中國、印度、伊斯蘭世界和歐洲)的科學知識和技術成果通過交流與融合,共同為近代科學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自主知識生產成為共識
加強自主知識生產成為打破“知識的終極闡釋者”幻覺的關鍵。全球南方國家推進自主知識生產的關鍵一步,就是擺脫對西方知識體系的依賴。
法勒進一步觀察到,全球北方國家和機構長期充當中介或守門人,把全球南方的知識生產擋在主流學術之外。因此,全球南方國家必須重新開辟一個空間發展自身的認知論。
費和平表示,具有自主性的知識生產將增強全球南方國家的主權與國際治理能力,為建設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添磚加瓦。
全球南方國家推進自主知識生產,既是根據本國的歷史背景、文化傳統與現實國情探尋發展道路,也是在政治與商業層面抵御西方現代化話語霸權。“自主思想的發展離不開政治主權與商業主權;西方攫取全球主導地位的手段一向如此:一面是軍隊與市場,一面是觀念與理論,二者一體兩面、不可分割。”費和平表示。
“如今,它們的繼承者——西方金融機構、資金雄厚的大學,以及企圖壟斷知識的學術期刊——正牢牢掌控著這套主導地位及其權力語法。這些現代全球秩序的‘神廟’不僅制定政策,更確立了一種理解世界的單一框架,一種界定正義、進步與自由的壟斷話語。這是一臺精密的剝削機器:金融機構與大學結盟,學術期刊為遴選的知識分子加冕。唯有打破這一循環及其背后的西方霸權,全球南方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參與才會從被恩賜的席位變為不可剝奪的權利。”費和平說。
西交利物浦大學國際研究系助理教授倪凱松(Niklas Weins)告訴記者,在自主知識生產共識的形成過程中,盡管情境各異,眾多學者仍將認知正義置于關鍵位置,堅持把知識深植本土經驗。另一個共同特征是對歷史不公的批判,范圍不僅涵蓋殖民主義,也涉及不平等貿易條件、環境外部性及知識等級論的現實后果。費和平認為,全球南方國家的學者共同譴責歷史不公,是因為殖民統治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并未隨形式獨立而終結,它借掠奪性經濟與學術依附延續——秘魯社會學家阿尼瓦爾·基哈諾(Aníbal Quijano)稱之為“知識的殖民性”。
多名學者表示,自主知識生產不是封閉主義和孤立主義。倪凱松提到,全球南方國家對自主的不懈追求并不是孤立主義,而是為本土方案與治理模式開辟空間。在巴西,這一點體現在農業生態學的研究中。在中國,生態文明理念反映出中國對根植于本土文化內涵的文明敘事的探索。這些經驗都表明,全球南方國家不僅是在回應全球北方國家,更在探尋內生性的替代路徑。費和平也認為,加強自主知識生產并不會使全球南方國家彼此孤立,反而將各國從被動接受單一思想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進而增進政治互信、促進民心相通。
共通的核心議題和理論關懷
全球南方國家在探索構建自主知識體系、搭建學術網絡的過程中,不約而同地凝聚起相似的核心議題和理論建構。費和平認為,全球南方國家的一個共同特征是其依賴性與自主、平等斗爭之間的歷史張力。盡管各國具體國情不同,但抵抗西方列強軍事侵略和占領行徑的共同經歷,催生出具有共性的認知框架,促進了全球南方國家間的思想交流。眾多核心議題和概念由此脫穎而出,在政治話語與社會理論中占據顯要位置。其中,現代化理論尤為突出。
“幾個世紀以來,隨著歐洲殖民勢力擴張,‘現代化’詞典都是由西方執筆編纂。”費和平說。談到現代化,法勒認為,對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性解讀不可或缺。“西方的‘現代—前現代’概念極易滑向另一組話語:西方的現代與非西方的前現代,而這種組合抹殺了現代西方和現代非西方的同時存在。結果是,全球知識生產的外部機制主導了對全球南方國家的想象,而后者的知識內涵、經驗與本土文化卻大多被忽視。”法勒解釋道。
來自全球南方國家的學者對西方現代化理論所謂“普適性”的批判一直存在。當塞內加爾歷史學家謝赫·安達·迪奧普(Cheikh Anta Diop) 重新確立非洲歷史的連續性,并揭示與亞洲的聯系時,當剛果(金)哲學家瓦倫丁·伊夫·穆迪姆貝(Valentin-Yves Mudimbe)拆解西方現代性依托的單中心的地理想象時,兩人都在否定西方現代性的普適神話。印度的“庶民研究”與拉丁美洲的“去殖民化”視角同樣提供了替代敘事。非洲孕育了最古老的知識,亞洲則以中國復興塑造未來。這幅多極時空圖景瓦解了歐洲中心主義,也終結了任何單中心的發展觀。
巴基斯坦瓦赫大學經濟學助理教授兼系主任阿蘇瑪·阿里夫(Asma Arif)向記者表示,在經濟學與發展研究領域,許多學者持續挑戰啟蒙理性主義衍生的西方普遍主義傳統,為全球南方探索獨立于西方的發展觀提供方法論創新。
“全球南方國家堅持走獨立、自主、可持續的現代化發展道路,是一種知識和政治上的去殖民化行動。”倪凱松說。費和平也表示,思想范式、價值觀和國家文化絕非點綴,而是關乎國家穩定與確保其在國際社會發聲的關鍵要素。全球南方國家之間的合作,以及從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到南南學術網絡的替代性多邊協定的建立,將決定重塑全球地緣政治知識版圖的能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劉雨微